从《诗经》看新诗形式建设的未来走向
——兼与陈仲义教授商榷
赵青山(山西)
近日阅读陈仲义教授发表在《河南社会科学》2019年5月第27卷第5期上的论文《现代诗:外形式的表征与体式——兼论“手枪体”与“截句体”》,文章认为:现代新诗外形式的标识是分行,也是它的外形式“底线”;如果不再坚守分行的“三八线”,散文诗有可能继续突破节、段、章的分隔,大量渗透到单句的分行排列,加剧模糊诗与散文诗的界限,实则有害于双方文体的各自建构;现代诗的外在形式只要遵守“分行排列”这一总体原则就行了。笔者读后产生了很大困惑。诗歌本是一种形式感很强的语言艺术,当现代新诗把诗歌艺术形式的诸多特征丢失殆尽,仅仅保留的唯一“分行”还要依靠诗歌理论家拼命维持,以证明其文体存在的时候,新诗还能够称得上“诗”这种高雅的语言艺术么?

一、仅仅把分行作为诗与散文诗的文体界限是不妥的
诗与散文诗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体,两者应该都有各自独立的文体特征。诗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上古的歌谣和先秦时期的《诗经》,具有铿锵有致的节奏和和谐流畅的韵律。散文诗大致诞生于二十世纪“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内容上追求短小隽永,形式上“随物赋形”。具体而言,在结构形式上,诗追求有规律地排列诗节诗行,散文诗追求不间断地联结语句;在语言表达上,诗追求“线”性概述,散文诗追求“面”性描述;在意境创造上,诗追求“虚”,讲究意在言外,散文诗追求“实”,讲究形散神不散。所以说,尽管现代新诗和散文诗在形式表征上还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即诗歌分行排列,但若仅仅将分行作为诗与散文诗的文体界限还是不妥的。因为现代新诗发展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将散文任意分行,并美其名曰“自由诗”,并且在诗学界获得了最广泛的认可。比如:

曾经平卧的南面滩涂,
涛声遵循着因果,由远而近。
一切都未曾命名。最初的一瞥,
用风水罗盘确定方位,
示现了五色恒星的初始兆瑞——
愿风调雨顺,
愿万物得以化育。
沧海桑田,还是南宋淳熙年间的盛事,
那时,人们的修为,
圣贫、精致,如花,如曼荼罗。
——韩高琦《蓬岛伽蓝记》节选
这是节选自微信朋友圈里的一节诗例,全诗四节,句式长短不齐,全诗没有一处押韵。若以陈仲义教授的“现代诗的外在形式只要遵守‘分行排列’这一总体原则”说而论,这无疑是一首现代新诗。但是这真的是一首诗么?这不是把散文分行排列了吗?类似的诗例,即便在《诗刊》、《星星》这些诗歌大刊之中也比比皆是。

其实,从散文诗诞生的那一刻起,理论家对其文体特征的界定就不在于是否分行,而是着眼于语言的描述性,着眼于散文诗独立的文体特征。1922年,愚庵(康白情)在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诗年选》中,对《月夜》作了这样的评论:“这首诗大约作于1917年的冬天,在中国新诗史上算是第一首散文诗”;①沈尹默的散文诗《月夜》发表在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上,全诗只有四句,但是在收入诗人诗集《月夜》时,却是分行排列的。如: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 沈尹默《月夜》
之所以说这是一首散文诗,是因为它虽然分行排列,但语句短短四句却长短不齐,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第三四句的语言也属于描述性语言;整体来看,也缺乏诗的形式美。
朱自清有一首著名的散文诗《匆匆》,如果分行排列,要比当今诗坛所谓“自由诗”不知要好多少倍。尽管如此,它应该依然还是散文诗。因为虽然前三行虽然诗行排列整齐,节奏匀称,但后面的句子却都是长短不齐的描述性语句了。如: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
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
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
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
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
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朱自清《匆匆》节选
为辨析诗与散文的文体特征,笔者曾经尝试用新诗来改写朱自清的散文诗《匆匆》。散文诗共五个自然段,改写诗五个小节。改写诗即使不分行排列,阅读时依然能够感受到铿锵的节奏,流畅的旋律,如果有人以其不分行排列就认定它为散文诗,恐怕大家不好接受吧?如:

燕子来了又去了,杨柳青了又枯了,桃花开了又谢了,匆匆的,春夏秋冬就逝去了
我的日子溜走了,你的日子溜走了,他的日子溜走了,匆匆的,日子它谁能留住呢
太阳升起又落了,吃饭走路睡觉了,我掩着面叹息了,匆匆的,日影儿眼前掠过了
一年年的消逝了,一月月的消逝了,一天天的消逝了,匆匆的,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赤裸裸的来了,赤裸裸的去么
——赵青山《匆匆》
由此看来,散文诗分行后还是散文诗,诗不分行排列也依然是诗。在当今将散文任意分行就称为“自由诗”的诗坛,现代诗的外在形式只遵守“分行排列”还是不妥的。

二、《诗经》是探究现代新诗外形式的源头
不少诗论家在讨论现代新诗的外形式时,常常将“自由诗”和“格律诗”放入一元论的语境中去言说。其建构现代新诗“格律诗”的参照大多为讲究平仄、讲究对仗、讲究古韵的律诗和绝句,其建构现代新诗“自由诗”的参照大多为不讲究任何语言规律,只遵守分行规则的所谓“分行体”。他们认为定行定字定韵定声的格律诗在现代新诗中举步维艰,此路难通;而肆意泛滥的自由“分行体”在当今诗坛欣欣向荣,能够引领现代新诗的建设朝向。且不说这些缺乏形式美的自由“分行体”能不能引领现代新诗,单是只凭借律诗绝句的格律形式为参照机械地来建构现代新诗的外形式,其视角就有很大的局限性。
我们知道,《诗经》是中华诗歌的源头,其铿锵有致的节奏与和谐流畅的韵律带给人们的审美习惯,传承了几千年,已经渗透到了民族的灵魂之中。建构现代新诗的外形式,应该追溯中华诗歌的源头,探究《诗经》的诗体外形式,以此为鉴,融汇到现代新诗的形式建设之中。那么,《诗经》中的诗体外形式究竟是怎样的呢?如: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
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周南·桃夭》
投我以木瓜,
报之以琼琚。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
报之以琼瑶。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
报之以琼玖。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
——《卫风·木瓜》
上述两首诗是《诗经》中最常见的两种体式,《周南·桃夭》全诗三节,整齐排列,句句押韵,节节换韵;《卫风·木瓜》全诗三节,每节之间对称排列,每节后两句押同字韵。纵观历代诗歌,诗行整齐排列,诗节对称排列,有规律地押韵,成为从楚辞、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曲这些具有形式美的诗体的共性特征。但是随着社会发展,语音体系逐渐成熟完善,唐诗宋词元曲又增加了平仄、对仗等格律元素并逐步定型,形成严格的格律诗。现代新诗能不能传承中华历代诗歌的诗体形式美?答案是肯定的。
早在新诗之初,有感于自由诗对新诗形式美的破坏,就有一批诗人聚集在一起进行新诗格律化的试验。他们办报纸,编刊物,进行规范和创制新诗体式的理论探索与创作试验,形成了追求新诗形式美的格律诗派——新月诗派。参照中华历代诗歌诗体形式美的特征,闻一多提出“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三美论,刘大白提出“整齐律”,朱湘提出“对称”论,陆志韦提出“重造新韵”,这些主张融汇在一起,就建构起了新诗最基本的两种体式——整齐体式和对称体式。这两种新诗体式要求遵循传统诗歌的审美习惯,要么整齐排列诗行,要么对称排列诗节,采用普通话“十三韵辙”,偶行押韵。至于其他方面,则诗无定节,节无定行,行无定字,这也就是闻一多《诗的格律》所言“律诗永远只有一个格式,但是新诗的格式是层出不穷”②的真实涵义。在试验层面,新诗人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作,成为新诗基本形式的典范。如: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绣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闻一多《死水》节选
全诗整齐排列,总计五节,每节四行,每行九言,偶行押韵,节节换韵。
小船呀轻飘,
杨柳呀风里颠摇;
荷叶呀翠盖,
荷花呀人样娇娆。
日落,
微波,
金丝闪动过小河。
左行
右撑,
莲舟上扬起歌声。
——朱湘《采莲曲》节选
全诗五节,每节十行,诗句虽然长短不齐,但节与节之间严格对称排列,有规律的押韵。
就这两种新诗形式的基本体式来看,诗行整齐排列与诗节对称排列、有规律地押韵等完全传承了中华诗歌的源头《诗经》,以及唐诗、宋词的美学特征。只是由于时代的变迁、语言体系的变化,新诗的形式蜕去了唐诗宋词中的平仄、对仗、古韵等格律元素,变得更加富有现代气息。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新月诗派确立了新诗形式的两种基本体式以来,百年间的诗体建设始终以“整齐式、对称式”为主体,在内涵与外延两个方向各自延伸和突破。一是内涵方向,在“整齐与对称”的基础上追求定行定言定韵,甚至定体,力求达到新诗形式美的极致;二是外延方向,突破诗体的整体格局,发掘新的美学意蕴。比如在一首诗中,整齐诗句与对称诗句交叉重叠的创作现象,对于新诗形式建设同样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

一个海员说,
他最喜欢的是起锚所激起的
那一片洁白的浪花……
一个海员说,
最使他高兴的是抛锚所发出的
那一阵铁链的喧哗……
一个盼望出发,
一个盼望到达
——艾青《盼望》
这首诗,第一节看起来象自由诗,但它和第二节完全对称,第三节只有两行,但诗行排列整齐。全诗三节,每节最后一行都押相同的韵,因此读起来非常和谐。这样的新诗体式既非整齐式,也非对称式,邹绛先生将其称为新诗形式的变体,万龙生先生将其称为“综合式”,后经以追求新诗形式建设为己任的重庆“东方诗风论坛”和成都“格律体新诗网”诗人群体讨论扩展,命名为“复合式”,最终形成新诗形式“整齐式、参差(对称)式、复合式”的“三分法”分类体系。在此分类理论指导下,重庆“东方诗风论坛”、成都“格律体新诗网”团结全国各地有志于新诗形式建设的诗人学者,经营网站论坛,编辑刊物,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坚守了近二十年,至今已出版纸质刊物《东方诗风》26期,《格律体新诗》24期,个人诗集有石家远《云松集》、陈建军《竹林集》、周琪《海棠新月集》、王民胜《为某个春天而写》、周思维《追梦路上》、张先锋《一路向前》、王世忠《林下听雨》、余小曲《余音未了》《视线内外》、龙光复《鹤皋秋影》、张静水《南庭集》、段永《脉络之间》、严希《履痕》、任雨玲《雨中百灵》等等。

“三分法”分类体系的意义除了首次对百年新诗纷繁复杂的诗歌现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类之外,还在于格律体新诗对现代“自由诗”美学追求的引领与提升。吕进教授在《三大重建:新诗,二次革命与再次复兴》一文中指出:“提升自由诗,成形现代格律诗,增多诗体,是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③其中“提升自由诗”引出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提升到什么程度,最高审美目标是什么?当今诗坛所谓“自由诗”的外在表征主要是:除了毫无规律的分行外,篇幅长段无规律,节奏押韵无规律。这样的“自由诗”,其美学目标是什么?我的理解是,“提升自由诗”的最高审美目标就是格律体新诗的新诗之美。具体地说,就是在一首诗中,追求诗句间的排比、诗句间的对称、诗句间的韵律等,使得一首诗在分节、分行、节奏、押韵等方面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凸显一种语言的秩序美。所以,具备格律体新诗的美学特征应该是自由诗的最高审美目标。
三、新诗体定型是有可能的
陈仲义教授认为:倡导新诗格律化的先辈诗人闻一多主张新诗的格式是量体裁衣,层出不穷,并且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匠随时构造。而“我们许多后续研究者,多把眼睛盯在外形式的诗形‘四定’上(定行/定字/定顿/定称)。实践证明,满足上述四大条律,几乎得交白卷。严格意义上的格律走不通。”(现代诗:外形式的表征与体式——兼论“手枪体”与“截句体”)④此种认识是因为论者对当今诗坛新诗格律化探索研究的现状缺乏深入了解所致。
正如前文所述,格律体新诗“三分法”分类体系和闻氏新格律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它本身就是对新月诗派新诗形式——整齐式和对称式——这两种体式在内涵与外延两个方向的延伸与突破。在外延方向的突破是发掘出了诗句内整齐、对称等交叉重叠的复合之美,成为格律体新诗分类之一“复合式”;而在内涵方向的延伸则是建构定节、定行、定字、定韵的定型新诗体。所以说,当今格律体新诗理论研究既关注闻一多等前辈诗人倡导的“量体裁衣”(整齐式、对称式、复合式),也关注建构定型新诗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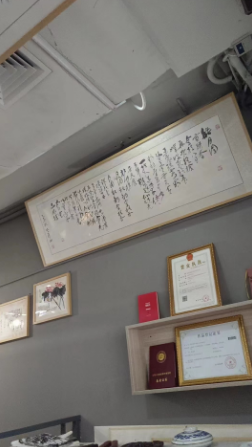
古典格律的精髓在于定型化。诗人们在长期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符合中国人审美心理的规则与形式,于是产生了律诗、绝句、词曲这样的脍炙人口的定型诗体。由于语言文化的发展,新诗脱离了原来的文言语法体系而采用了全新的现代汉语,新的艺术形式当然也有这种追求,也追求定型新诗体的多样化,更追求这种规则和形式的固化和推广,并且也把它作为新诗艺术成熟的标志。因为诗体定型的实质就是把能够提升新诗艺术美的语言技巧固定下来,诗体一旦定型,就具有了严格的艺术规定性。诗人们也会因为在同一形式中的反复多次的实践,艺术功力易于更快地趋于成熟。所以诗体定型既是提升新诗人艺术功力的试验田,也会成为检验新诗艺术形式美的试金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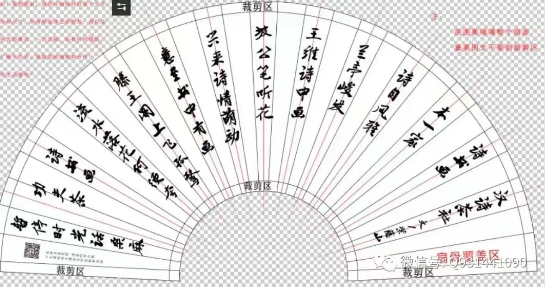
定型新诗体,不是随意规定出来的,而是通过对百年以来的新诗创作进行分析、概括,归纳、总结出来的。它要求在坚守“整齐、对称、押韵”的传统诗歌美学意蕴基础上,通过大量定行诗、定言诗、定韵诗的创作实践,加以融汇,选取既符合中华民族传统诗歌审美习惯,又为广大诗人读者喜闻乐见的诗体形式,加以倡导推广,进而逐步定型。

当今诗坛尝试的较为成熟的定型新诗体有:
1、汉俳
汉俳,是借鉴日本俳句体式而形成的一种三行小诗体。每首诗格式固定,三行分别是五、七、五字,押同一韵,还可以根据需要组诗联排。此种诗体虽然使用古典诗词中常见的五七言句式,但摆脱了古诗词中平仄、古韵等的束缚,运用现代语言,运用现代汉语的节奏规范,也呈现出了新的诗体形态。湖南诗人段乐三,2002年筹建益阳市汉俳诗研究会,创办《汉俳诗刊》(季刊),2004年改名为《汉俳诗人》,截止2008年,共出版24期(终刊)。长春汉俳学会于2009年成立,并创刊《汉俳诗刊》(季刊),每季度出版一期,截止2020年已出版26期。已出版的汉俳诗集诗论集有王中忱《汉俳吟草》、张玉伦《双燕飞 汉俳诗百首选》、刘德有《旅怀吟笺 汉俳百首》、邵麟茜《汉俳吟》、 黑天一羽《汉俳365首》、李增山《汉俳三百首》、曹鸿志《汉俳诗五百首》、晓帆《汉俳论》等。
二、柔巴依
柔巴依是一种规范严谨的四行体世界性格律诗体,九、十世纪出现并广泛流传在古代波斯和中亚操突厥语人民以及我国新疆维吾尔族、塔吉克族人民中间。自上世纪“五四”前后传入中国以来,新诗人纷纷对其进行译介,试图将其引进并改造成为一种新的格律诗体,译诗形式也异彩纷呈,如潘家柏的无韵散文体形式,孙毓棠的韵体新诗形式,李霁野、黄克荪的五七言绝句形式,赛福鼎的十一言新格律形式等等,而黄杲炘先生的译诗独具匠心。具体要求为:一、运用规范的现代汉语。二、原诗每首四行,译诗也每首四行。三、原诗每行含抑扬格五音步(十音节),译诗也每行由五个音组(即顿、拍子或拍)构成以代替原诗的五个音步。四、限定每个诗行为十二个汉字,即要求这十二个汉字构成五个音组。五、在押韵方式上一承原制,体现了柔巴依译诗的中国新诗格律化过程。进入新世纪,以重庆、成都为核心,并辐射全国的格律体新诗人以黄杲炘先生的柔巴依译诗体为标准,创作了大量全诗四行,每行十二言,句句押韵(或偶句押韵,或一二四句押韵)的柔巴依新诗,他们还运用这种短小精悍的诗体酬和唱答,掀起了柔巴依诗体的创作高潮,使得柔巴依逐步成为现代汉语格律诗的一种成熟的定型新诗体。已出版或结集的柔巴依诗集有(波斯)哈亚姆著,张晖译《柔巴依诗集》、黄杲炘译《英汉对照·柔巴依一百首》、哈尼扎特·海尤拉尼著《一百个柔巴依》、张静水《闲月集·柔巴依100首》、万龙生《涉诗柔巴依62首》等等。
3、十三行新汉诗
十三行新汉诗是深圳大学黄永健教授自2013年推出的一种定型新诗体,全诗十三行,依次按33、44、55、66、77、337言格式排列,隔行押韵。这种诗体格式固定、字数有限、行数有约。语言上采用了中华传统诗歌常见的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形式,因排列形态形似手枪,还赋予了一个形象的名字手枪体(也称松竹体)。近年来,黄永健教授不仅团结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年轻诗人试验创作这种新诗体,而且积极撰写论文,探索这种诗体的格律诗学理论,出版了诗集《新汉诗十三行体·手枪诗集》(2015年)。该课题还获得了2019年“当代汉诗创新诗体研究”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同时在深圳光明区、江苏盐城、广东兴宁等地创建十三行汉诗艺术创作基地,出版诗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第一次将新诗体同书法、绘画、商品有机融合,大大拓宽了新诗体的传播途径。已出版的十三行新汉诗诗集还有《姜桂诗集》等。

4、十四行诗
又称“商籁体”,是一种跨域传播的世界性格律诗体。发源于意大利,流行于14至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大陆。16世纪中叶传入英国,不久便风行于英国诗坛。说它是一种格律诗体,是因为它有固定的诗体形式:一有固定的行数,不能多也不能少于十四行。二有固定的诗节,或者由两个诗节(8、6),或者由四个诗节(常见的意大利式为4/4/3/3,英国式为4/4/4/ 2)组成。三有固定的韵式,意大利式十四行体前八行中的两个四行组用抱韵,后六行中的两个三行组变化较多,但也有一定规律;英国式十四行体前面三个四行组用交韵,最后两行用偶韵。四有固定的音步,英国十四行诗多为每行轻重格五音步。法国十四行诗多为每行十二音。这种十四行诗体,诗句整齐、短小精悍、格律严谨、富于极强的音乐效果。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新诗人如闻一多、孙大雨、卞之琳、唐湜、杨德豫、屠岸、冯至等纷纷对其进行译介,试图移植为中国的格律新诗体。新世纪以来,新诗人在遵循“整齐式、对称式、复合式”三分法分类体系基础上,将其改造为86式、4433式、4442式三种体式,采用偶行押韵的方式,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新诗特色的十四行格律诗体。已经出版的诗集有万龙生《八行十四行诗百首》、王端诚《十四行宋词今译》《微斋十四行》、石家远《定行诗选》、郑泓《十四行诗选集》、邹惟山《汉语十四行实验诗集》等。
5、花环体
十四行花环体是历史上欧洲诗人在长期监禁中反复琢磨才定型的一种诗体,其主要特点是在组诗之中追求蝉联重叠,勾连成章。全诗共十五首十四行诗,前14首的首行和末行顶针相联,即后一首的第一行用前一首的最后一行,上下衔接,第14首的末行用第1首的首行,从而勾连成环状,而每首诗的第一行合起来,又串成第15首,首尾相连由此得名“花环”。
十四行“花环体”虽然是舶来品,但是这种诗体自二十世纪初,伴随着“十四行诗”传入中国后,就受到不少新诗人的喜爱。新诗人陆续尝试写作,逐渐在诗行排列、韵律规范等方面融入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习惯。从韵律来看,虽然不乏交韵、抱韵等,但以偶句押韵、一韵到底为主。从表现内容来看,有抒情诗,如金波《献给母亲的花环》是写给母亲的颂歌,韩晶宇《玉花环》是献给父亲的寿礼;王端诚《秋菊之歌》反映的是当时都城社会习俗和贵族人士的文化生活情趣;也有叙事诗,如高红武《剑侠与刀客》等。因此,这种诗体已成为现代新诗的一种较为成熟的新格律诗体。

受益于十四行花环体新诗格律的启发,新诗人根据其格律规则尝试创新了四行花环体、六行花环体、八行花环体的诗体试验。如八行花环体新诗的格律规则为:每首诗八行,九言(或十言),共九首诗。前八首每首第一行为前首末一行,最后一首末一行为全诗第一行。每首诗第一行又可组成一首九言八行新律诗,成为第九首。全诗整齐排列,偶行押韵,循环往复,勾连成章,故可称为八行花环体新诗。其它四行花环体、六行花环体的格律规则以此类推。

已编辑出版的花环体诗集有赵青山主编《十四行花环体新诗选》、赵青山诗集《向律而歌——八行花环体新诗集》。
上述这些诗体,汉俳、十三行新汉诗趋向于古典格律改良方向,是蜕去平仄,古韵以后的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句式在新诗生态中的改造与运用。柔巴依、十四行趋向于外来诗体归化方向,是外国格律诗体与中国传统诗歌审美习惯的融汇与贯通。花环体更是中西合璧、格律更加严谨的现代新诗体臻品。新诗人同时还在进行六行体、八行体等定型新诗体的尝试,如万龙生《六行弦歌集》、高昌《高昌八行新律》等,它们都是符合“定节定行定字定韵”的标准格律诗,参与创作的诗人成千上万,每种诗体都出版了具有各自独特诗体特征的诗集,所以说陈教授文中所言“满足诗形四定(定行/定字/定顿/定称)四大条律,几乎得交白卷”⑤的论说是站不住脚的。

陈教授的文章还认为:古诗的外形式相对单纯,由于严谨的行联、字数、平仄、韵辙规定,任何造次、怪异的秩序都会立马被逐出诗歌行列,这种认识就更加值得商榷了。大家翻翻《唐诗三百首》,里面除了七律五律、七绝五绝以外,不是还有五言古诗、七言古诗吗?不是还有李白的《将进酒》、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吗?它们不是也不完全符合律绝格律的唯一标准,也没有被踢出唐诗以外吗?《唐诗三百首》的选者并没有用律诗作为唯一的标准来衡量旧体诗,里面既有律诗绝句,也有排律,还有歌行体等,这种选诗标准为我们启示了新诗形式存在的基本形态:新诗的形式建设既追求符合中国传统诗歌审美习惯的“整齐式、对称式、复合式”的基本形式,也追求形成承载中国诗歌美学极致的格律诗体,宽严相济才是新诗形式存在的健康状态。
注释:
① 徐成淼著,散文诗的精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10,第3页
② 林文光选编,闻一多文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04,第69页
③ 吕进,熊辉主编,诗学 2009 第1辑,巴蜀书社,2009.09,第11页
④《河南社会科学》 2019年第5期 P34页
⑤ 同上。

版权说明:如非注明,本站文章均为 紫藤山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和附带本文链接。
本文暂时没有评论,来添加一个吧(●'◡'●)